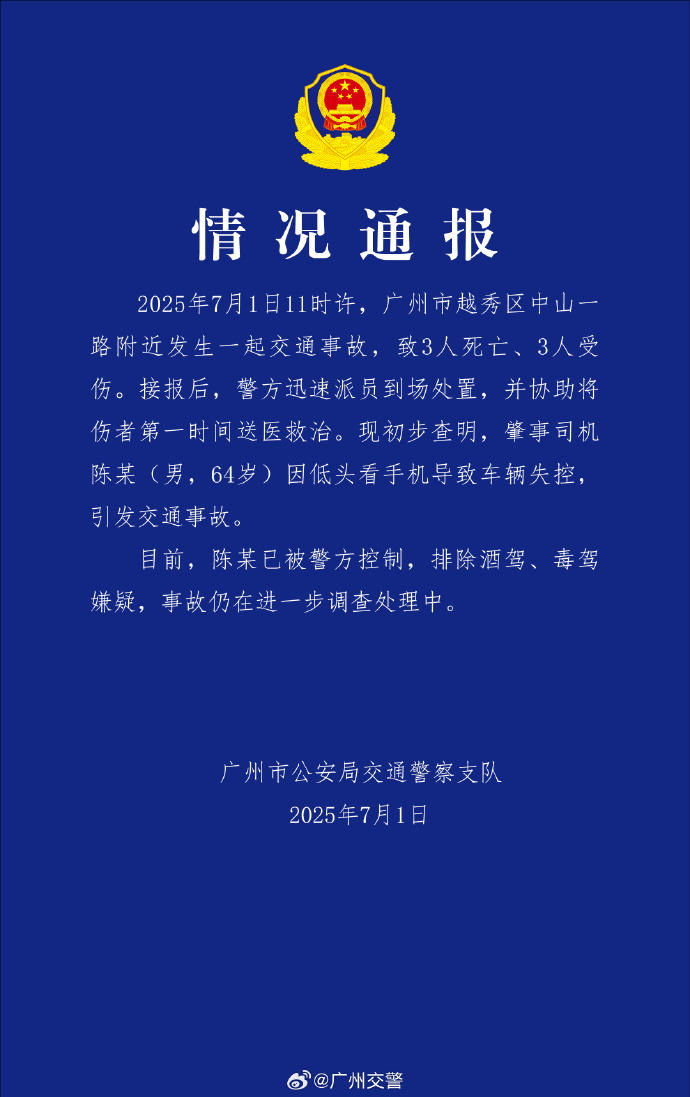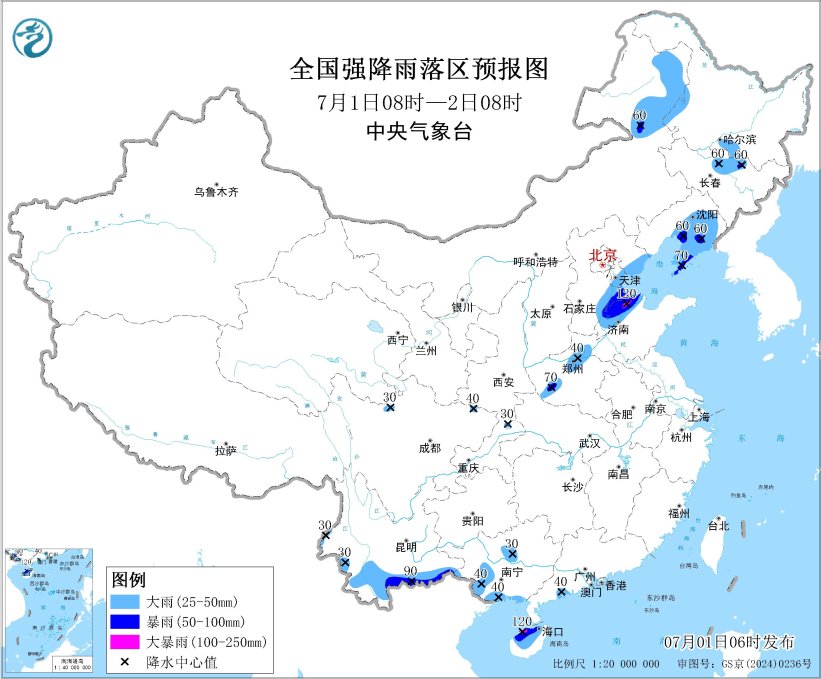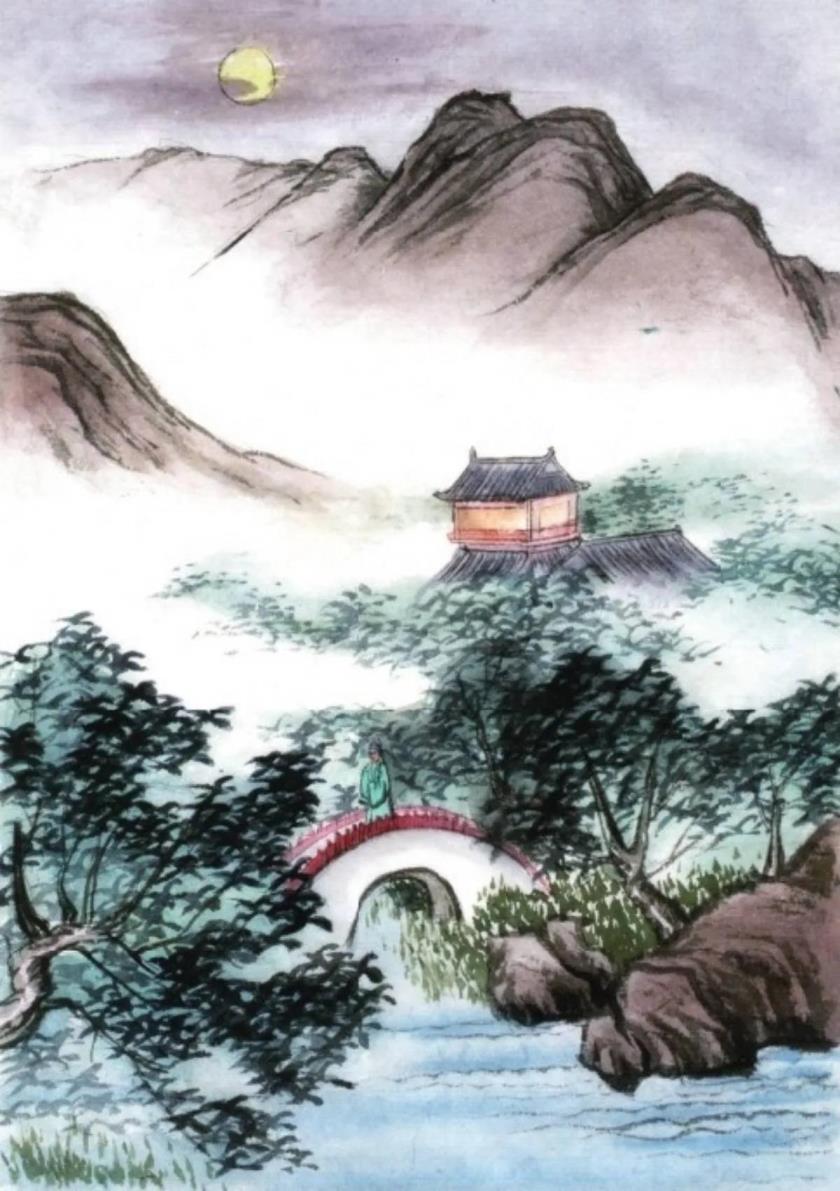留不住年轻人,算什么好城市?
时间:2025-07-01 11:00作者:
Z是字母表的最后一位,却是年轻世代的代名词。Z世代流向哪里,哪里就是站在所有城市之前的“第Z城”。
第Z城是卡尔维诺笔下“看不见的城市”,由看不见的风景组成:清风拂过人们年轻的脖子,巷子里飘满咖啡的味道,满城的绿植正在进行光合作用,其中的人也在吸收生活的养分。
但第Z城并不抽象,它是具体而可抵达的生活方式:更有朝气的经济,更多元的城市文化,更可接受的生活成本,更适合年轻人生活与发展,不浪费年轻的热忱与才情。
也正因此,第Z城是重新找回城市本质的城市代名词,它是建筑、自然、诗歌和音乐的四位一体,拒绝单一,拒绝无聊,唤醒生而为人的可能性,正如查尔斯·兰姆所说,“如果你醒着,生活就醒着”。
如何创造一座第Z城,答案已经不言而喻了:去问一问年轻人的感受,让他们的快乐不再是奢侈品,忧愁不再是无解的考题,让他们的获得感根植于看得见、摸得着的体验。
再问一问自己的内心:那些你愿意为之逗留和徘徊的城市,那些你愿意让下一代成长于其中的地方,就是你的第Z城。
请记住这个数字:1222万——这是2025年即将毕业的应届大学生的数量。即将离开校园的他们,会更愿意选择在哪座城市开启新生活?或者,反过来说,城市应该怎么做,才能成为年轻人的“理想型”?
自2016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《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》以来,全国多座城市推出人才引进政策,掀起“抢人大战”。其中,西安、武汉、成都、杭州等“二线明星城市”成为主角。
此后,一轮轮的“抢人大战”热潮不退,除了表现最积极的二线城市,一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也纷纷入场。
2025年开年,北京、深圳、上海等地接连出台“抢人”新政。为正在求职的应届毕业生提供免费短租是基本配置,2018年就实现大学毕业生引进“秒批”的深圳,此次喊出“只收梦想,不收租金”的口号。
“抢人”,就是抢人才,尤其是创业人才。DeepSeek创始人梁文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:“我们并没有什么高深莫测的奇才,都是一些top高校的应届毕业生,没毕业的博四、博五实习生,还有一些毕业才几年的年轻人。”
而最新这一轮的“抢人”,更倾向于以产业“抢人”,按需“抢人”。比如,广东省的“百万英才汇南粤”行动计划,首期募集超过60万个岗位,半导体、人工智能、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岗位占比超七成。
各地对年轻人才的争夺,归根结底是对城市未来的争夺。
什么样的城市称得上“青春之城”?年轻人的“理想型”,现在有个新名称叫“青年友好型城市”(youth-friendly city)。因为青年的发展性特征,又称“青年发展型城市”。更直白地说,就是“青春城市”或“年轻城市”。城市要发展,青年首先要发展,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共识。
2022年4月,我国开始进行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。首批入选的试点名单中,除了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,重庆、天津、杭州、苏州、成都、武汉、长沙、贵阳等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的城市也在列,共有45个试点城市(含直辖市的市辖区)、99个试点县域。
试点两年来,来自中国共青团网的数据显示,截至2024年年初,在第一批试点城市引领带动下,已有超过200个地市、近500个县域主动参与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。从“抢人大战”到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,可以说,政策正在向年轻人倾斜。
什么样的城市称得上“青春之城”?2014年,加拿大战略咨询公司Decode发布了其第一份全球“青春城市排行榜”(YouthfulCities Index),在入榜的25座城市中,多伦多、柏林、纽约排在前三位,上海排在第20位,是唯一入榜的中国城市。
青春城市联合创始人索尼娅·米尔科维奇(Sonja Miokovic)表示:“全球有一半的人口不到 30岁,他们中的一半居住在城市中。年轻人和城市——尤其是大城市,这两者共同创造未来。城市需要符合年轻人口味,并且让他们积极释放潜能。我们所处的时代充满机会,年轻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未开发资源,他们可以改变我们的居住环境、工作地点和娱乐方式。”
在青春城市团队看来,更年轻的城市普遍表现为六大特征,即联结(connected)、活力(dynamic)、开放(open)、新奇(curious)、创造(inventive)和好玩(playful)。他们的评选,即围绕生活(live)、工作(work)、玩乐(play)这三个核心维度展开。比如工作维度,通过就业、金融服务、教育、创业、可负担性(物价和房价)这五个二级指标加以测度。
国内也有类似评选。福卡智库评选“青春之城”,基于“创新、活力、有为、品质、开放、有爱”六大要素;半熟财经则通过就业吸引力、生活成本、生活便利度、政策支持力、人文吸引力这五大维度评选“年轻力城市”。
在2024年半熟财经发布的“年轻力城市”榜单中,广州、北京、杭州、南京、上海排在前五位。广州综合排名第一,跟它在生活便利度(排第一)、人文吸引力(排第二)、就业吸引力(排第三)这几个子项的突出表现密不可分。
年轻人在哪里,人气就在哪里2023年春节,知名科技博主阮一峰在长沙、昆明、大理度假,这些城市旺盛的人气,让他始料不及。
在长沙,大年初一当天,黄兴路步行街的每一个摊位都在排长队。他在一家茶饮店排队20分钟,终于轮上,店员才告诉他,还要再等90分钟才能做好饮品,他以为听错了;在昆明,因为他出门晚,市中心的昆明老街没有饭店可以吃饭,饭店都说排队的客人满了,不再接单;在大理古城,晚上10点,许多城市的夜市已打烊,而这里的夜市刚刚开始,人头涌动,看样子直到午夜都不会停息。
阮一峰现居上海。在他看来,上海就见不到这样的人气,尤其是春节期间,人都走了,更是冷清。为什么像上海这样的有着约2500万常住人口的超大城市,人气反而不如这三座城市?阮一峰认为,这跟人口的年龄结构有关。
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,这四座城市老龄人口(60岁以上)的比重,昆明最低(14.40%),长沙(15.33%)、大理(15.80%)次之,上海则最高(23.40%)。街头消费的主力军是年轻人,而上海老龄化现象严重,所以街上人气不旺。
不仅仅是上海,沿海省份的老龄化程度也普遍高于内陆省份。与此同时,内陆省份不仅老龄人口比重低,出生率也更高。长期来看,内陆的年轻人口会大大多于沿海,消费需求也更强——因为消费增长主要由年轻人推动。阮一峰据此认为,这些年轻人口旺盛的需求,就是中国下一步的增长动力。
2022年,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、原副院长何建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表示:“一座城市的活力永远来源于受过良好教育的,有理想、有追求的年轻人。”在何建华看来,一线城市现在也开始有未来焦虑症,“如果(城市)每年没有一定比例的新鲜血液注入,同时又快速步入老年化,那么这座城市无非是‘未富先衰’,或者说未来发展的动力、动能和潜力不足”。
“蹲”一个适合自己的城市把人“引”过来之后,更重要的是让他们“留”下来。
从以往的“送户口”“送补贴”到现在的“送短租”,有评论指出,许多城市在制定吸引年轻人的策略时,还在用“70后的思维解00后的方程”,没有跟上他们的步伐。
2022年,DT财经和小红书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联手发布《“蹲”个城市——年轻人选择城市新需求洞察报告》。其数据基于DT财经发起的“你的理想城市是啥样”小调研,共有2025人参与调研,其中00后、95后和90后占比近九成(86.60%)。
该报告发现,有82.10%的受访者有换个城市生活的想法,而且他们会主动寻找宜居城市。比如,2022年年初以来,小红书开始涌现“蹲一个宜居城市”的相关笔记。报告团队对这些笔记进行分析,得出20个宜居城市需求关键词,房价、交通、高铁、便利、医疗排前五位。此外,还有一些个性化需求:“几线都行”“水果城”“适合宅”“对宠物友好”“有Livehouse”“古建筑多”“丰富的戏剧展览”,等等。
也就是说,城市的硬性发展指标依然重要,房价、收入这种经济指标,以及高铁、机场、地铁、教育和医疗资源等基础设施,年轻人都会考量;但在常规标准之外,年轻人显然对生活细节提出了更多明确的要求。
调研数据也佐证了这一取向。在回答“如果要选择未来居住和工作的城市,你认为城市的哪些特点更加重要?”这个问题时,受访者的选择往往是“物质和精神都要”——在生活性价比、居住便利度、工作机会、交通便捷度之外,交友氛围、文化娱乐活力、商业发达度、生活新鲜感也很重要。
而在对不同城市特点的重视程度上,有着年龄差异:85后认为“文化娱乐活力”非常重要的比例仅为19.90%,00后中占比则达到40.70%;而认为“交友氛围”非常重要的比例,00后(36.70%)也比85后(25.00%)高。
“他们跳出了原本的城市流动框架,不再将自己局限在大城市和老家的二选一难题里,广阔天地处处可去;他们打破了他人定义的优秀城市标准模板,按照自己的需求来设定理想目标;他们变被动为主动,网上冲浪打捞寻找适合自己的落脚点。”该报告如此总结。
(图/《灿烂的风和海》)
哪些城市满足了Z世代对物质和精神的双重需求,就能赢得他们的心。
举个例子,成都利用城市高架桥下的空间、废弃厂房等城市闲置的空间,打造“金角银边”,为青年提供运动、休闲、健身的场所。在成华区桃源社区,街道和小区之间的闲置空地被改造成免费开放的体育小广场。还记得去年的“成都迪士尼”吗?它本身不过是位于玉林七巷一处居民区的一块健身器材区域。没准这两块健身区域还能形成某种联动呢,是不是很有趣?
而对于附近的居民来说,在锻炼身体之外,那里还可以成为一个和邻居碰头的微社区中心——这就是学者们所说的“找回附近”。
(图/《灿烂的风和海》)
由此,人们才会真正感受到,这是“我”的城市,是心甘情愿住下来、成为家乡的地方。